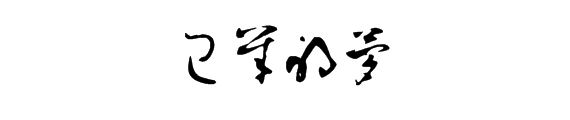【选段】
在某一个晚上,我在海边遇到一个陌生女人。女人赤脚站在栈桥粗糙的石台面上,黑色的轻纱裙摆在黑夜中像是风的化身在我眼前摇动。还未入夏的海边夜晚总是有些凉的,我打了个颤,或许是因为冷,也或许是因为我将要与这个女人说话。
“你不冷啊。”
我冲她喊着,却似乎没发出什么声音。
她像是早就知道我会与她说话一般,向着远处将一切都隐匿起来的海的深处说:“冷啊!”
“那你为什么不下来啊!”
她回过头来看着我,她的脸与黑暗融为了一体,我想借着月光、栈桥边昏暗的灯光以及月亮照在海面上反射出来微弱的光看清楚她的脸。长发挡住了她脸的轮廓,也吸引走了所有的光。
【正文】
在一个暮色还未从窗台离去的傍晚,我从梦中醒来,梦中混乱的景象与眼前即将消散的红色相接,让我一时间分不清自己所看到的红色窗影是梦的倒影还是现实。在瞀乱的记忆迟迟不能归至麻木的身体之前,我看到桌子上静静躺着的一张白色信封。
我独居许久,除了我,没人进过这间幽沉的屋子。
然而这封信却在我未完善的记忆中缺失了它的位置。我记不清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似乎它自始至终就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从未注意过。
信封上没有署名和地址,只是在信封背面的折页处,记录了一个时间——二零一七年八月。
三年前的信。
我猜想也许是南将它放在这里的。
南是一名作家,如同这个职业的大多数人一般,她在深夜写作,白天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我打电话给她,电话那边不断循环的占线声让我觉得自己在等待一个不会出现的人。我挂断电话,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询问她是否在我这留了一封信。
几天后,南出现在我的家里。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放了几听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罐装雪碧,瓶身上的白霜映出南白皙的面庞,我们两个弯曲的脸排列在一起,像是在绿色画布上创作的一幅印象派油画。
南笑我:“你可真小气,我来你家,你就请我喝饮料!”
南问我有酒吗,她告诉她马上就要走了。我问她要去哪里,她还没想好,只是要离开这座城市,去创作一部她构思了很久的小说。
“什么小说?”
她打开一听雪碧,“嘶~”,仰起头,混杂在饮料中的柠檬味气泡顺着喉咙吞下去,若隐若现的喉结跳动地向下传递着,我看到她的胸脯起伏。
“《巴别塔》。——你的雪碧太凉了,还是给我来点酒吧。”
我去冰箱里拿来一瓶起泡酒,握着它长长得瓶颈,寒意透过瓶身笼罩了我的手心。
“你果然够小气,这个又喝不醉。”
南接过酒瓶就要摇晃起来,我赶忙夺了回来,我说你要是摇完了可自己去门外启酒,别喷得我家里到处都是。南冲我笑着说她已经摇完了,让我启开。我撕开密闭的锡箔纸,轻轻拧了两圈瓶盖上的铁丝,小心翼翼的将木塞旋转着向外拔出。“嘭”,木塞飞到了天花板上,又坠落到地上,泡沫顺着瓶口喷在了我的手上。南笑弓了腰,她的衣领随着笑声晃动着。
我找来一只高脚杯,清黄色的酒沿着透明杯壁滑进酒杯里,密稠的气泡自淡黄色的杯底向上翻涌,空气中渐渐弥漫着轻微的葡萄味果香。
“你好像是要庆祝我离开。”
“《巴别塔》是什么?我听着耳熟。”
“‘巴别塔’是圣经里的一座塔,意思是通天之塔,是人们为了到达天堂而修建的一座塔。”
“那你小说里写得是什么?”
南抿了一口酒,眉毛微蹙了一下。
“好酸!”
“还是喝雪碧吧。”
“我有一天午睡——午睡前我都喜欢看一会书。”
“嗯。”
“那天正好看到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小说中有这么一段,大概是说有一个学者实地考察过巴别塔建造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巴别塔的地基太弱,而长城才是巴别塔真正的基础。”
我说我不太明白。
“你想啊,如果要建一座真正的通天之塔,那么塔足够高,地基也就需要足够大,而长城是全世界最长的建筑,那也只有长城才足够做巴别塔的地基。”
我点头。
“但这也不够,我接着又想,那最极限的办法,就是绕地球一圈,把地球圈起来。”
“嗯——”
南喝了一大口酒,我听到她喉咙里发出的“咕咚”声。
“我一边睡觉一边想,我看见我站在那座塔上。塔越垒越高,结果,塔塌了。”
“塌了?”
“嗯,我一下子就醒了。我意识到,塔的地基足够长还是不行,还得足够宽,最好每一寸土地都是巴别塔的地基。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了吧?”
我没有回答,我想象不出来。
“但还是不行,因为这样的话,我建起来的塔每一厘米都是从土地上取来的原料,而取来的原料又堆在了每一寸土地上,结果就是这座塔一厘米都不会增高。”
“这——”
“我想创作一个种族的人,这个种族天生的使命就是建造巴别塔,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这是他们的与生俱来的使命。不过他们永远也造不出来这座塔,他们世世代代就在建造巴别塔中消耗完一生。”
我问她为什么。
她看看我:“他们还最起码还有一个使命,还有一件事要做。你要做什么呢?”
“不知道。”
“小说中的人哪里知道,他们世世代代奋斗的事情,只是我午睡时偶尔冒出来的一个念想。”
南将淡黄色一饮而尽。
送南离开我家的时候,我跟在南的身后,她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拥抱我,我闻到了她身上的淡黄色味道。
南临走时,我想到那封信,便问她是不是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没有,还笑着说这个年代了谁还会写信。
我估摸着她要告别这座城市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传来的却又是只有无法接通的提示声。于是我发信息,祝她成功。她也没有回我。
在黎明将至之时,我又将睡去。我的如丝絮一般缠绕的梦里总会伫立一面高耸的墙,我在这面墙落下的巨大阴影中徘徊,抬头向上望去一眼看不到顶,向两侧望去也没有尽头。墙体似乎也并不是直立的,无论我站在哪里,它都像是要向我倾倒而来,我总是被压迫的喘不过气来。
又一个傍晚,微弱的敲门声惊扰了我缥缈的梦。一个男人站在我的门前,在我惺忪的睡眼中,他如一缕烟雾一般轻盈虚幻。他喃喃地告诉我,他是南的朋友,南临走时怕我孤单,将我的地址留给他,嘱托他来找我。我将他请进屋里,他径直走进了我的房间,在我还未来得及反应之前,自然地坐到我的书桌前,熟稔的程度好像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我家,而那个座位本来也应该是他的。我不由得在这位客人的面前显得局促起来,似乎我才是这间屋子的客人。我跟在他的身后走回房间,询问他是否需要喝些什么。他说不用麻烦了,我看到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桌子上的那封信。我给他倒了杯水,放到那封信的旁边,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我觉得奇怪,就继续问他那别人怎么称呼他。
“你就叫‘你’就好,我叫我自己就叫‘我’。”
我只当他不想告诉我,便不再追问。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继续说些什么了。他还在看着桌子上的信封。
“那你是哪里的。”
“不知道。”
我更加觉得新奇,我说你没有家吗?
他没有回答。
于是我也不再主动开口说话。
沉闷。在屋顶暗黄色灯光的照射下男人的影子在隐藏在黑夜中的玻璃上分裂成了两个,又合并成了一个。我从窗户上看着男人消瘦的脸,男人的眼睛也透过玻璃在冷冷地盯着我。
“你看过这封信吗?”男人说话了,可我似乎并没有看到他的嘴唇有颤动过的痕迹。
“什么?”
男人拾起信来,翻看着信的正面和背面,那上面没有字,他却像是在仔细阅读信封的内容一般,目光飘过信封的每一个角落。
“这信上也没有署名和地址。”
“嗯?我不知道这是谁寄来的。”
“我也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不过我已经看了。”
说完,就要把信封打开。我赶忙抢了过来,压在了堆放在桌角的书下面。
“你还没看吧。”
男人直直得望着我,我在他的眼睛中看不到我的影子,便不由得错开眼神。
“南小说写得怎么样?”
南不写小说了?
为什么?
“我得走了。”
男人一下子站起来。我赶忙拦住他。
“那她去哪了?”
“不知道。没人知道。”
男人没再说话,也不再看我,如同到来时一般,径直离开了我的家。
此后的几天里,我都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担心男人的再次拜访和不辞而别。
我常去海边坐着,在太阳消失之后,感受从海的深处吹来冰冷的风,像冰片一般撕开肌肤的感觉总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着的。然而当我向风吹来的方向望去时,却什么也看不见,黑色与黑色连成一片,我又觉得什么又都是不存在的。时间是虚无的,它原本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人们对一个又一个白天黑夜的无休止循环的一个刻度。无尽总是可怕的,在永远探索不到的地方隐藏着人类对未知最深处的恐惧。于是,时间有了终止,白天与黑夜合为了一体,却与第二日的白天与黑夜彻底决裂。四季成为了一个轮回,人们选择其中的一天,将其画上了句号。而人的生存与死亡也清清楚楚得分出了界限。在人类真正有时间这个刻度概念之前,他们看到的世界也许与我们会有不同吧。蝴蝶由生至死,并不是因为时间凋零的缘故,而仅仅是因为蝴蝶这个个体,或者说由某种物质组成的这个生命,不断变化,从原始的无,到有,到生长,到凋亡,再到无。而日落日出,也仅仅是因为物体的运动。甚至包括人的本身,并非是因为时间的逝去而生老病死,也只是遵从了物体原本的变化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看,空间则要真实得多:一个永恒存在的整体,它承载了一切的变化,所有变化对它来说微不足道。至此,死亡变得不再那么可怕,它只是空间中的某件物质,从一种形态到另一个形态的链接。而死后的个体,依然进行着变化,只是形状、样貌、结构,还有思想都不再相同。它或许还是它,或者,它本来就不是它。
在下一个傍晚,我忽然意识到那可能是南留给我的辞别信,就打开了信封。
不是南的笔迹。信写得很杂乱,每一个字都如同画上去得一般。这封信更像是一个从未习字的孩子用从没有握过的笔对照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临摹上去的。有些字我还依稀能辨别出来,但另外一些字我就完全看不懂了,似乎用的并不是汉字的笔法,而只是凭借脑海中对这个字的理解在纸上涂抹出来。断句也没有什么规律,有些标点符号甚至标在了字的中央。
信不长,但我看不懂。信得格式倒是与普通信的格式并无二致,只是信得称谓与落款用得又是那一套完全看不懂得笔法。或许,这原本就只是一出恶作剧,是谁留在我这儿的一个无意间的玩笑。
往后的日子里,我总是在傍晚醒来,在黎明睡去。
其实在傍晚时醒来是有好处的。我总会在太阳离开之前醒来,睁开眼,就会看到光明与黑暗交汇的地方,这是我一天之中我最感觉不到时间的时刻,此时,我是永恒的,是构成了空间的某一部分。而通常这个时候,往往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所有的感觉器官都不再工作,我与光明黑暗完全融为了一体。而当黑暗完全降临,我又不得不去将电灯打开。这时,我又会发现,时间是无比真实的存在,而且飞快。
我曾问过南为何要写小说,她说生活太过于苦闷了,小说是她唯一能逃离现实世界的媒介。况且,她也想在无垠的岁月中,留下一些自己的印记。
我笑她,我说她写不出好的小说。
她问我为什么。
我问她这篇小说为何一定要是她写呢?任何一个人,在任何的时间,都可能写出与其一样的小说。这篇小说一旦完成,它的存在便只是存在,与任何人都不再有关系,与谁写的它也没有关系。而之后的时间中,或者说空间中,这篇小说都只是这篇小说本身。她却是有可能真真切切得不存在了。即使她不存在了,“东西北”也有可能写出来完全一样的小说。小说又与她何干,无非是人们在小说的最后,再回过头来看一眼这篇小说是谁写的,或者像一个小说评论家一般站在高处品头论足一番。人们评论的终究是这篇小说的“作者”,一个只是与她名字相同的代号。
她说如此便不是她写得小说了。
“你在写小说的时候能真实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吗?”
她说不能。
我说我也总是不能感觉到自己存在着,我的生命就像是一个躯壳,承载着我的情感和意识,但情感和意识总会有消亡的一天,甚至它们还不如我的躯壳真实,因为躯壳总会以不同形式永生。
南说不是。她在写小说的时候,虽然并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但她知道,她的思想是真实存在着的,这似乎与现实的物理世界正是相反。只有这种办法——她在小说中构建她的世界时,她的思想才可以留存下来。而她的思想也只能是她的思想,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人有与她相同的思想,“东西北”都不可能。所以她的小说只能由她来创作。即使有人创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小说,那也完完全全是不同的小说,因为它承载的思想完全不同。而就这个道理而言,她又说,于是她相信,她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永存的,与空间同在,不会消失在虚无的时间中,因为她的思想会留存,会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思想中,而那个人或许又会用相同的思想,影响另外一个人,那样,她才是真正的永生。
男人没再来过,或许是第一次见面,我待他过于冷淡了。
没人再来找过我,男人不来了,南也不来了。
我意识中唯一还存在可以与外界连接的方法,只剩下那一封信。其实我从未停下思索那封信的主人,只是他太过于虚幻,太不真实,他就像是介于梦与现实之间的一个影子一般若有若无,每当我想探寻他的踪迹,他便将自己隐匿起来。以至于每次我想到他都只是在心中匆匆掠过,就强迫自己去想别的事情了。或许是他寄错了人,又或者记错了人。
在某一个晚上,我在海边遇到一个陌生女人。女人赤脚站在栈桥粗糙的石台面上,黑色的轻纱裙摆在黑夜中像是风的化身在我眼前摇动。还未入夏的海边夜晚总是有些凉的,我打了个颤,或许是因为冷,也或许是因为我将要与这个女人说话。
“你不冷啊。”
我冲她喊着,却似乎没发出什么声音。
她像是早就知道我会与她说话一般,向着远处将一切都隐匿起来的海的深处说:“冷啊!”
“那你为什么不下来啊!”
她回过头来看着我,她的脸与黑暗融为了一体,我想借着月光、栈桥边昏暗的灯光以及月亮照在海面上反射出来微弱的光看清楚她的脸。长发挡住了她脸的轮廓,也吸引走了所有的光。
“你拉我下来吧。”
我伸手。
她把胳膊放入我的手心,我握不到她的骨骼,只有潮湿而凉爽的感觉。我不禁又打了个颤。
我们沿着海边散步,光着脚踩在沙滩上,看脚印被海水冲走。也许南是会在时间中留下印记吧,但是我的印记呢?我没有办法像南一样,将自己的思想种在另一个人灵魂中肥沃的土壤里。我只能像脚印一般,短暂的在这个世界停留。然后,被时间凝聚而成的海水冲走。
“信你看了吗?”
女人的声音像是随着入夜的海风从远处飘来。我惊奇的转过头望向她,可我依旧看不到她的脸。也或许是我看清了,只是她的脸与无数个陌生的脸一样,在与我相遇后,又立刻从我记忆的屋子里退了出去,隐匿在我记忆外,如同无数的我曾看过,曾听过,曾思考过却已经不会再回到这间屋子中的匆匆行人一般。也许我若是从记忆的屋中走出去,亦能找到她,只是我也无法确认那是不是她,或是另一个与她相似但完全不同的曾出现在我记忆中的人。
那句话似乎并不是她说的,但那的确是她的声音。
“什么?”我想询问她,确认是她将这句话留在了海边。
她却像是没听到我的声音一般,笑着向海里跑去,她的笑声像是清脆的闹铃一般,终止了我无休止的念头。她呼喊着我,让我随她一起钻进墨色的海里。
冰凉的海水不停地从脚掌刺破我的肌肤,钻进我的血肉里,用细小的针尖扎着我的骨头。我只得不停地抬起脚跺着水花以此驱赶寒冷。女人看我窘迫的样子笑得更开心了。她过来抓住我的手腕,向更深的海跑去,我没有挣脱,随着女人踉跄着向海得深处跑去。
当我们再坐到沙滩上时,女人的裙边已经被海水浸过,紧紧地贴在大腿上。她腿上和手臂上的水珠清晰可见,倒不像是海水,更像是从皮肤下渗出的颗粒状的汗水。我觉得口干舌燥。
她用沙子堆砌了一个简陋的城堡,说是城堡,其实更像是一所四面漏风的茅房。她说那是为我建造的,我就住在里面。我笑笑。她说也许可以是真的。我觉得冷,就拉着她离开了海边。
坐在路灯下的长椅上,她告诉我其实她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与她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已经成家的男人。男人此刻也许正在酒店里睡觉,也许正在与他的妻子通电话。男人已经四十多岁,她与他的身体并不相配,不过这也不太影响什么,男人有别的办法让她到达高潮。只是他们上床之前,她一定要让男人将他的妻子从通讯录里删掉。我说这也改变不了什么,她无法代替被删掉的那个人,她说她只要在那一刻,男人是属于她的,她就可以当作那个人没有存在过,男人也可以暂时忘记除了她以外的其他人。
我独自坐在条椅上,目送女人的背影渐渐从幽黄的灯光下淡出,消失在黑暗中。我终究没有看清女人的脸,她依旧只生活在别人的世界,对我来说,她仍然是一个陌生女人,陌生到若是我第二次遇见她,我也只会当她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人。
回到家,我忽而想起女人留在海边的话,我竟然忘记询问女人为何知道我收到了一封信。我再次打开信,吃力地将每一个画符还原成字的模样。渐渐,我晓得了其中一些字的含义,然而这些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拼凑在一起的字,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就像是一个人乘着一辆飞驰的汽车穿梭在一座城市之中,目之所及的随便一个字,就记录下来,然后抬起头来看到的另一个随便的字,再记录在刚才那个字的后面。我完全弄不明白这封信具体是在讲什么,即使我像玩拼图游戏一般将这些字全部拆开,又按照所有可能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却仍然不知所云。不过我似乎从中看出来大概信的主人在什么时间见过我,并且想要通过这封信向我表达友好的问候。但我没有任何印象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么一个奇怪的人,更想不明白在我认识的人中为什么会有人要写这样一封奇怪的信。我思索着所有与这封信相关联的人,却只有那个陌生女人突如其来没缘由的话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声音在记忆的改变下变得具象起来,那句话不再只是通过听觉留在我能找到的地方,而更像是电影一般,在我脑海里不停地回放。也许那不是我第一次见她,而只是我以为我是第一次见到她。
在下一个春天来临之前,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南的名字。南并没有像她所说的一般,让她创造的族人陷入永世轮回之中。她最终还是让他们建成了那一座通天之塔,让他们见到了“神”。所见方式便是用她的口吻写了一封信,信中,她向她创作的角色解释了建造这座塔的意义。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意义,所有的意义也仅仅是南的自说自话罢了。但小说中的人们却为了我看上去明明没有意义的事拥有十足的动力,并且在巴别塔建成之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与满足感。我感到惊奇。小说的最后,南在信中写到,她相信时间,她也相信自己是时间中真实存在过的人。而她创作的这些生命(他们也相信她的存在),也只能是由她创造。
倏然,我想,我应该给南也写一封信了。
信写好了,我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就放在了桌子上。
后来,那封信不知所踪。
再次见到南是在一个罕见的清晨,我破天荒的没有在日出之时睡去。我走在海边,太阳此时刚从低于海平面的位置露出来,将隐藏在黑暗中的远离陆地的海面缓缓点亮,海的表层皱起鲜红色的波纹。渐渐地,海面之上的红轮与隐藏在海中的倒影完美的拼接成一整个太阳,随着波浪的涌动破碎、拼接。当海面的颜色完全变成金色时,我向着太阳的方向,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影。阳光直射入我的眼中,我看不清晰,黑色的剪影中我只能看到她随晨间的风飘动的发丝。我走上前去,咸涩的海风从剪影的背后吹来,在风中还有隐约得淡黄色味道。
好久不见。
我们沿着海边走着,没有什么目的地,还没来得及熄灭的路灯将我们两个的影子浅浅地印在地上,拖得长长的影子在远离我们身体的地方悄悄地离开了。
我祝贺她小说发表成功。
南咯咯地笑着:“可是我的小说并没有发表啊。”
又是我与时间相悖的记忆发生了混乱。
“我在书店看到了你的名字。”
“也许是另外一个叫南的作家写了一篇同样的小说。”
南说她走的疲惫了,便将胳膊挂在我的胳膊上,身子倾斜着将体重分担于我一些,她柔软的胸部不时地触碰到我的关节。
我问她那她的小说呢?
她说她也不知道它的命运,她赋予了它们生命后,只是将它托付给了没有回信的杂志以及将一切抛弃的时间。
“那你写给主角的那封信呢?”
她很惊讶,问我如何知道她写了一份信。
我说我的确是在书店中看到了她的名字,并且读了她的小说。
她说我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现了偏差。
“那封信在某个清晨,就消失不见了。”
她忽然又像想起来什么似的,抬头对我说:“你给我写得信我也收到了,只是我看不懂你写的是什么。”
我对她说没什么,紧接着我又向她问起来去我家里的那个男人。
南说她并没有拜托什么人造访过我。我向她描述男人的长相。
“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你描述的好像是我小说里的主人公。”
当我们走得疲惫不堪,便像是在心里达成了共识一般将这次散步的终点设置在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南再次向我道别,并告诉我这一次她不会回来了。
我向她郑重告别。
南说她的确在空间上留下了印记,但时间不属于她。
此后,我没再见过她,她从我所在的空间中彻底消失了。脚印一般,没留下任何痕迹。而我又相信了时间,因为我总能在时间上,找到与她重逢的机会。
我想起我与南相遇的时间,是三年前。
南是我笔下的一个人。
是以我妻子原型刻画的一个人。
可我在时间线上,却没有找到我的妻子。我再往前找,也没有发现其他人。我终于发现,在这条时间线上,只有四个人,我,南,那个男人以及似乎并不存在过的陌生女人。
我回到了家,捡起桌子上的那封信。
现在我知道,这份信的主人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