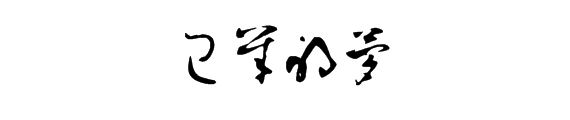【选段】
而此时男人是什么表情呢?我又看了他一眼,只见他仰着头,安然地靠在座椅上,仿佛这车里的一切与他们无关。阳光落下,洒在他的脸上和婴儿身上,他眼角的泪痕在金光中闪闪发亮。此刻,他真的像一个母亲一般,坦然地让孩子吸吮着自己的乳头,他也像是等待着,等待着这车比婴儿还聒噪的人,能停止“啼哭”,找到他们自己的奶头。
【正文】
十五年前夏天,我去坐长途汽车。这种长途车如今不多见了,但那时几乎全是这种车——白色的车身在炎热的天气里犹如一块脏兮兮黏糊糊的奶块,行李全堆在车顶的行李架上,车里的人也像这些行李一般,挤在不足三十平米的密闭盒子里,盒子唯一能与外界流通的地方,就只有被颠簸地“扑棱”响的车窗敞开的一条缝。这种车不跑高速,它通常往返于几座相邻城市之间,有时还会从半道上再往车厢里塞几个人。
我坐在倒数第二排靠过道的一边,旁边坐了一个肥胖女人,大半个屁股已经跨过了座椅边界放到了我的椅子上。我被挤到一边,身体尽量不挨着她,但摇晃的车身让我偶尔碰到她白花花的手臂,她胳膊上的汗蹭到我身上。我暗暗用劲,想将女人挤回到她的位子上去,然而女人像是没有知觉一般,对我的动作毫不在意。过了一会,她从掖在车座底下的包里抽出一根玉米,自顾自地啃了起来。
过道的另一边坐着一对父子。父亲三十来岁的样子,身上的衬衫皱皱巴巴,头顶的头发根根竖立着,两侧的头发也向外扎煞着,胡子像是一根根黑色的针浓密地扎在下巴上。他后脑勺顶在椅背上,眼睛闭着,身子不时向一侧倾去,还没等到完全倒下,就赶忙支起身子,头继续向后顶着。他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婴儿穿了一身红色的长袖花衣,脸紧贴父亲的胸脯,头枕在父亲手肘上,整个身子窝在他手臂里。婴儿的眼皮也合着,他静静地躺在父亲怀里,偶尔扭动一下身子,或转动一下脑袋,胳膊有时也会抬一抬,胖乎乎的小手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一样,攥起拳头,接着又松开。两个人身体紧贴着,我看到父亲的胸口灰色衬衫已经被汗洇透了,婴儿却毫不在乎地将脸贴在汗渍上。
原本的沉闷与安静被司机的急刹车打破了。我身旁的女人头磕在前面座椅上,刚啃到嘴里的玉米粒吐了一地,嘴里嘟囔着“哎吆喂”;头靠在车窗上、顶在椅背上、倚在别人身上,身体倾泻着的,口水滴到裤子上的,从鼻子里和嘴巴里打着呼噜的人纷纷坐直了身子,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向前张望着。只见从车前门上来一个穿着蓝色西装,戴着金框眼镜,有点秃顶的男人,刚刚被打扰了清梦的人嘴里嘟哝着什么,身子又软了下去。售票员赶忙站起来,几步来到车前,随着已经发动的车子摇晃着身体,扯着嗓门喊道“你去哪?”,男人低声向她道出目的地后,售票员又大声告诉车厢里所有人“十二块五!”,随后,领着男人向后走来。走到我身前站住,指着那对父子说:“就这一个位儿了,你坐这吧。来,你把行李拿一下。”
父亲也在刚才的刹车中醒了过来,他看向孩子,只见孩子舒展了一下四肢,也要醒过来。他赶忙轻轻摇晃手臂,所幸孩子只是歪了一下头,又继续睡去了。可售票员的声音立马又在耳边炸开,婴儿开始不安分地扭动身体,哭声也呼之欲出,父亲摇晃的手臂已经不起作用。正是这时售票员走到这对父子身边,指着他们让他给这个西装男腾个地方。
婴儿的哭声已经先于他醒了过来,他没有睁眼,五官全挤在面庞中央,嗓音从刚开始的沙哑变得洪亮。将梦破碎的铃声在每个人耳边响起,人们纷纷回过了头,皱着眉头望向这个父亲。他无奈地看了看售票员,左手摇晃婴儿,轻声说“没事没事”,右手从婴儿身下抽出来,提溜起旁边座椅上的包塞到了座位下面,然后小心地抬起屁股,往右挪了挪,坐到了刚才放包的位子上。
售票员已经走回去了,父亲向西装男讪讪地笑了笑,西装男没有低头,用眼睛瞥了他一下,没立即坐下,而是将包放在座椅上,在里面翻腾半天,从包的底部抽出一条耳机,耳机底端还连着一个mp4。他将耳机塞进耳朵里,mp4装进兜里,这才把包提起来,坐下,又把包放在身上,闭上了眼睛。
父亲冲前面回过身来的人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然后埋下头,一边继续摇晃着手臂,一边用低沉的嗓音轻声哄着孩子。然而婴儿的啼哭声更响了,哭声断断续续,每次停顿都仿佛是为下一次更用力的开始做准备。婴儿此时已经不能安分地躺在手臂上了,他扑腾着身子,想从父亲怀里挣脱出来。父亲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然而他只是重复着“听话,不要哭了”之类无用的话。
醒来的人们又纷纷回过了头,售票员的屁股也从座位上离开,弓着腰向后面看来;有挨着坐的两个人交头接耳,一边说一边用眼角向后瞟着,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跳动着;有的人没有说话,瞪圆了眼睛,嘴撇到一边半张着,两个眉毛中央锁住,向上挑着;有个小男孩,完全转过了身子,跪在椅子上,他脑袋光溜溜的,眼睛珠子也溜溜地转,好奇地望着这对父子,嘴巴咧开,嘿嘿地笑,他妈妈拍了拍他的屁股,让他坐下,别回头,他坐下后还时不时把头扭过来,从两个椅子中间的缝向后看过来。我身旁的胖女人晃悠了一下屁股,身子向前蛄蛹了蛄蛹,探出脑袋来,目光从我身前略过,瞅着父子。西装男摆弄了半天mp4,耳机从耳朵里拿下来又塞进去,最后侧过身子,用背盯着男人,胳膊交叉环抱在胸前,继续闭着眼睛,皱着眉。
婴儿似乎是哭得有点累了,声音比之前小了一点,但仍没有停下的意思。父亲把手伸进婴儿衣服里,摸了摸婴儿后背,嘟囔着:“出了这么多汗,应该是热了。”说完连忙把手抽出来,解开婴儿衣领胸前的几个扣子,又弯下腰,从包里摸索半天,掏出来一把断了翅的蒲扇,一边轻轻拍打着婴儿的脚,一边给婴儿扇着风,“啰啰,不哭了,凉快了,不哭了啊。”
婴儿的情绪缓和了一点,但没过多久,哭声又响了起来。原本情绪也稍有放松的人们一下子又紧绷起来。父亲哄孩子的语调变得着急,风扇得越来越大,甚至吹到我这里,我都感觉凉快了一些。然而婴儿这一次没有要停下的意思,“难道不是热了?”,父亲咕哝着。他又摸了摸婴儿的背,已经没有汗了,他自己却已经满头汗了。
他想了想,将蒲扇放到一边,掀开婴儿的裤子,解开尿布,瞅了一会,又合上了。
“也没尿啊。”
男人又将手伸进包里,我看着那个黑漆漆的布包,琢磨着接下来他会从里面掏出什么。他的手还没拿出来,就听到“布噔布噔”的响声,这种鼓锤快速敲击两个面发出两种不同声音的独特响声,不用看就知道,那是个拨浪鼓。拨浪鼓在他手里旋转着,鼓锤像被线拴住的两只蜜蜂,绕着鼔身飞来飞去,他将拨浪鼓放到婴儿眼前,用声音吸引婴儿的注意。这的确好使,婴儿止住了哭声,瞪圆了湿漉漉的小眼,伸手就要去够拨浪鼓,父亲在婴儿即将碰到之前,忽然将拨浪鼓升高,飞到天上去,婴儿“咯咯”地笑起来,身子都快要坐起来,两只小手向上抓着。哭声止住了,然而人们厌烦的情绪并没有因此减弱,西装男又向过道这侧探了探肩膀,用很轻的声音,但足以我和那个父亲听到“妈的”,紧接着又提高了声音,用司机都可以听到的音量叫到:“有病吧!”那父亲赶忙从空中收回了胳膊,低下头,小声地对西装男说:“对不起,对不起”,但他手里的鼔却没停下,只是转动的幅度小了很多,声音也轻了许多。西装男像是没听到,并不搭理那个父亲。这时婴儿的注意力已经从拨浪鼓上离开了,他仰着头,望着身旁这个穿着整齐、头发稀少的男人,挂着泪痕的脸上绽开笑容。
但没多久,婴儿脸上的表情变了,笑容消失了,眼睛和眉毛、鼻子和嘴巴又要挤在一起。父亲赶忙将拨浪鼓递到婴儿手中,婴儿没握住拨浪鼓,他只是抓了一下就松开,拨浪鼓已经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哭声又一次响起来,而且急促得多,这声音就像暴雨来临之前,在闷热空气中猛然炸开的惊雷。我身旁的胖女人扭动着身子,喘着粗气,抓着前面的座椅,猛然站起来,我赶忙向外倒了一下身子,给胖女人腾出一点地方。她站起来吸了两口气,用比哭声还高的嗓门,冲那父亲喊道:“吵死了!管管你小孩!”我感觉左边耳朵生疼,像是要被震裂开。女人吆喝完,一屁股坐回到座子上,座位晃动了一下,我真怕她这一屁股把座位坐塌了。从车前侧也传来一些声音,只是没有胖女人嗓门那么大:“真是,这可真烦人,觉都睡不好了。”、“也不知道管管孩子”、“是不是饿了啊”。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车里热闹了起来,男人把头埋得更深了,脸涨得通红,衣服已经被汗浸湿了一大片。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又在包里掏了起来。这次他掏出来一个保温杯、一个奶瓶、一罐奶粉。他一只手抓着奶瓶瓶身,用大拇指和食指旋开奶瓶盖子,再将奶瓶夹在两个膝盖之间,奶瓶盖放到大腿上;用屁股和车窗下面的沿儿夹住奶粉盒,掀开奶粉盒盖子,捏着奶粉盒里的小勺挖了两勺倒进奶瓶里;拧开保温杯,往奶瓶中倒了些水,摇晃几下,再将奶瓶灌满,拧上瓶盖。他倾斜着奶瓶,将奶嘴塞进婴儿嘴巴里。婴儿立马止住了哭声,含着奶嘴咬了起来,他的两只小手像是要抓住奶瓶一样,向上够着。父亲终于喘了口气,身子像是被抽去骨头一般松懈下来,车前厢的人看到婴儿没了动静,脸上也都一下子没了表情,回过了头。
车厢里的忽然安静让我感到不适应,仿佛刚才我所处的是另一个与现实割裂的空间,而现在婴儿停了啼哭,沉闷又一次降临,车里唯一的动静又只有被震得不停响的车玻璃声,倦意再次袭上了人们的眼皮。
“又开始了,有完没完!”
婴儿的哭声再次响起,人们这次彻底没了耐性,前车有几个人站了起来,作势就要向后走来。西装男也不再闭着眼,他站起身,提着包,就向前车走去,走到司机身后,一屁股坐在发动机盖子上,这次他不再装作睡觉了,而是和其他人一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父亲。
父亲从婴儿将奶嘴吐掉时身体就开始变得僵硬,他将奶瓶放到一边,低下头,藏在前面车座后面。这次他没再管婴儿的哭泣,也没理会前面那些人的叫声,眼睛空洞地望着他的孩子,整个人抖了起来,那不像是哄婴儿时的摇晃动作,而是因为紧张或情绪激动,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人们被他奇怪的举动惊呆了,本来骂骂咧咧的人话说了一半,半张着嘴,像个痴呆一样望着他。我也把头埋到座椅下,歪着头看他,想看他到底是什么表情。我看到他偷偷瞄了我一眼,又立即将眼神收了回去,过了一会,又向我瞄了一眼,看到我还在看他,就拿手擦了擦脸,吸了两下鼻涕,歪过头来冲我笑了笑。说那是笑,倒不如说是咧了一下嘴准确,因为他完全没有笑意,眼睛、眉毛、甚至腮帮子全都是向下耷拉着,他的眼里蒙着一层水雾,眼底噙着泪,眼角已经有了泪痕。我赶忙也冲他笑了笑,但我知道,我的脸上也没有丝毫笑意,更多的是如同其他人一般吃惊的表情。他立马又把头扭了回去,我看到水滴落在了婴儿的花衣上。
车厢里没了别的动静,只剩下婴儿的哭声,人们像是被定住身子一般,看着父亲,想不通他为何像是发病了一般不停抖动。
忽然,父亲停止了抖动,身子也再次松弛下来,他像做了什么决定一般,长吁了一口气,熟练地解开衬衫纽扣,掀开衣服,又从包里取出一块叠放整齐的毛巾,展开,用叠在里面的那一侧,擦了擦胸膛。他弓下身子,将婴儿向上抱了抱,婴儿立刻停止哭泣,把脸埋在他的胸膛里,咬住他的乳头,吸了起来。
车厢安静了下来,似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人们惊呆了,站在原地,随着汽车的晃动摇晃着身子,嘴巴一直半张着。
“啊!变态!”
我身旁的胖女人尖叫一声,她的声音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人们耳朵里,一下子惊醒了所有人。人们开始叫起来,大声讨论起来,“变态”声不绝于耳。西装男这时冷静地转过身,靠到了司机身旁,跟司机说了什么。汽车戛然而止,停在了半路,他又掏出手机,靠在耳边,嘟嘟囔囔说了些什么。挂了电话后,他缓慢地站起身,抓着扶手走到售票员身边,停了两秒。
“静一下,大家静一下。”
西装男的声音不大,但语气中透露出一种威严,人们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摒着气,听西装男要说什么。
“我已经报警了,大家稍安勿躁,配合一下,等一会,警察马上就来,抓走这个变态!”
西装男说完,人群立马炸开,有欢呼的,有的喊早该报警了,也有的人不耐烦地说那得等多久啊,人群中有几个坐着的人,小声嘀咕着没必要吧,但声音立马就被盖了过去。
西装男看到人们的反应,很满意地回到发动机盖子上,塞上耳机,继续坐着了。
胖女人无疑是人群中最聒噪的一个,她已经跨过我的身子,走到车厢前面,同一个卷发大婶讨论着什么。
我没有说话,男人眼中隐蔽的泪滴在我心里,我猜想着泪的来由,不禁同情起了男人。
而此时男人是什么表情呢?我又看了他一眼,只见他仰着头,安然地靠在座椅上,仿佛这车里的一切与他们无关。阳光落下,洒在他的脸上和婴儿身上,他眼角的泪痕在金光中闪闪发亮。此刻,他真的像一个母亲一般,坦然地让孩子吸吮着自己的乳头,他也像是等待着,等待着这车比婴儿还聒噪的人,能停止“啼哭”,找到他们自己的奶头。